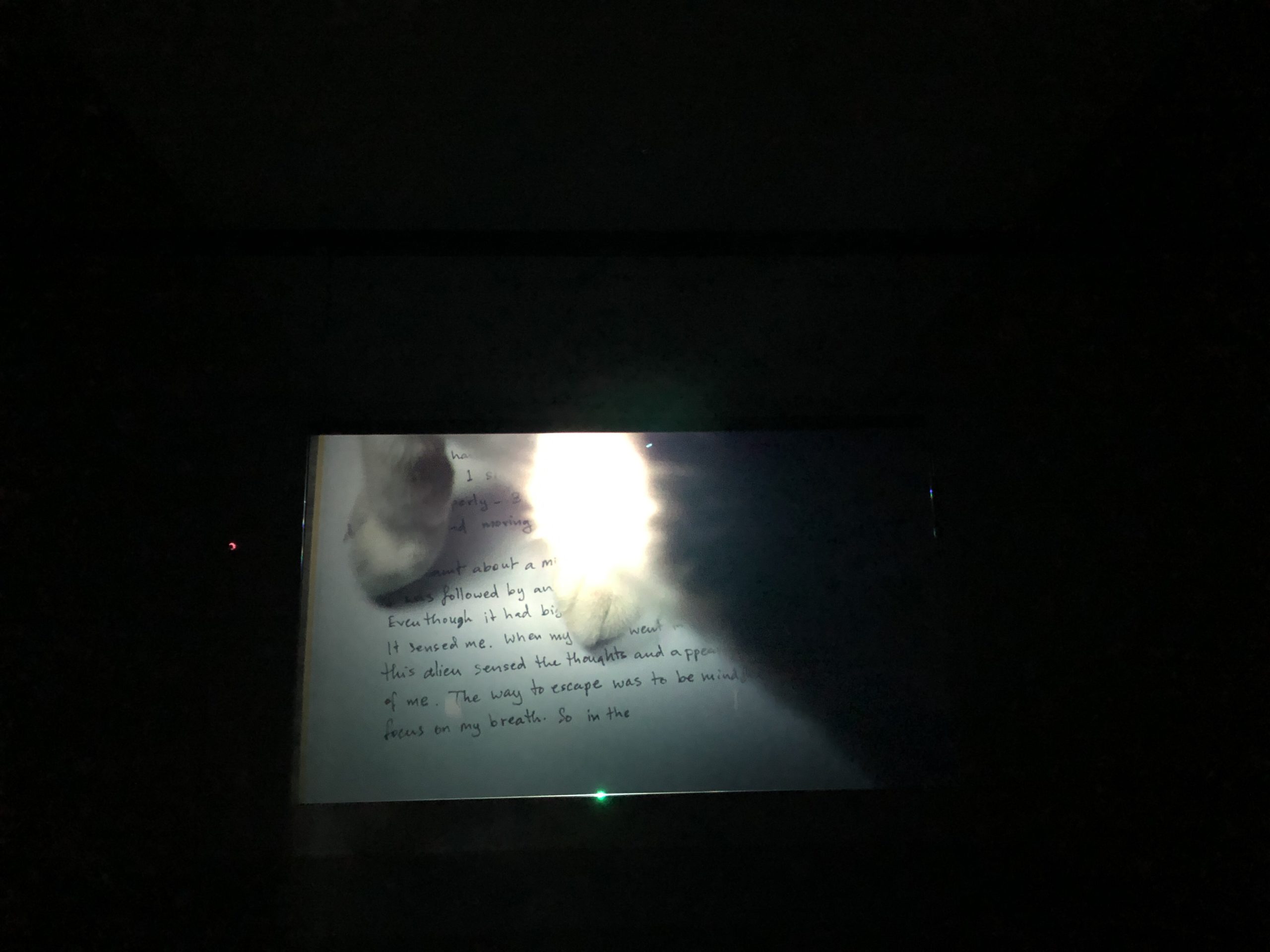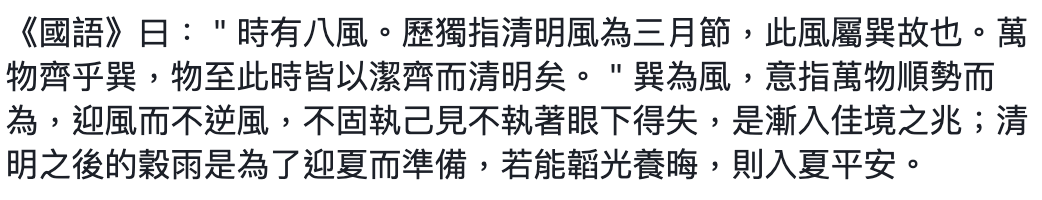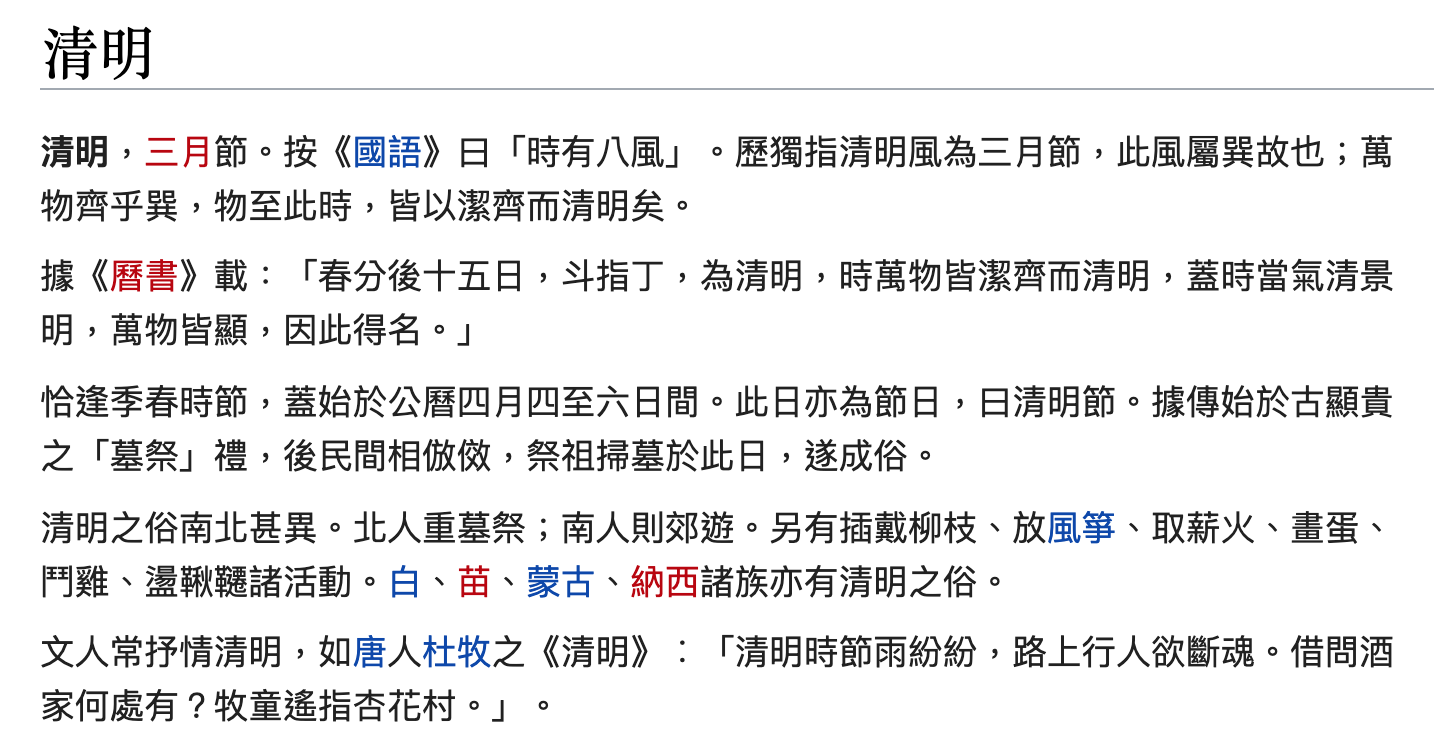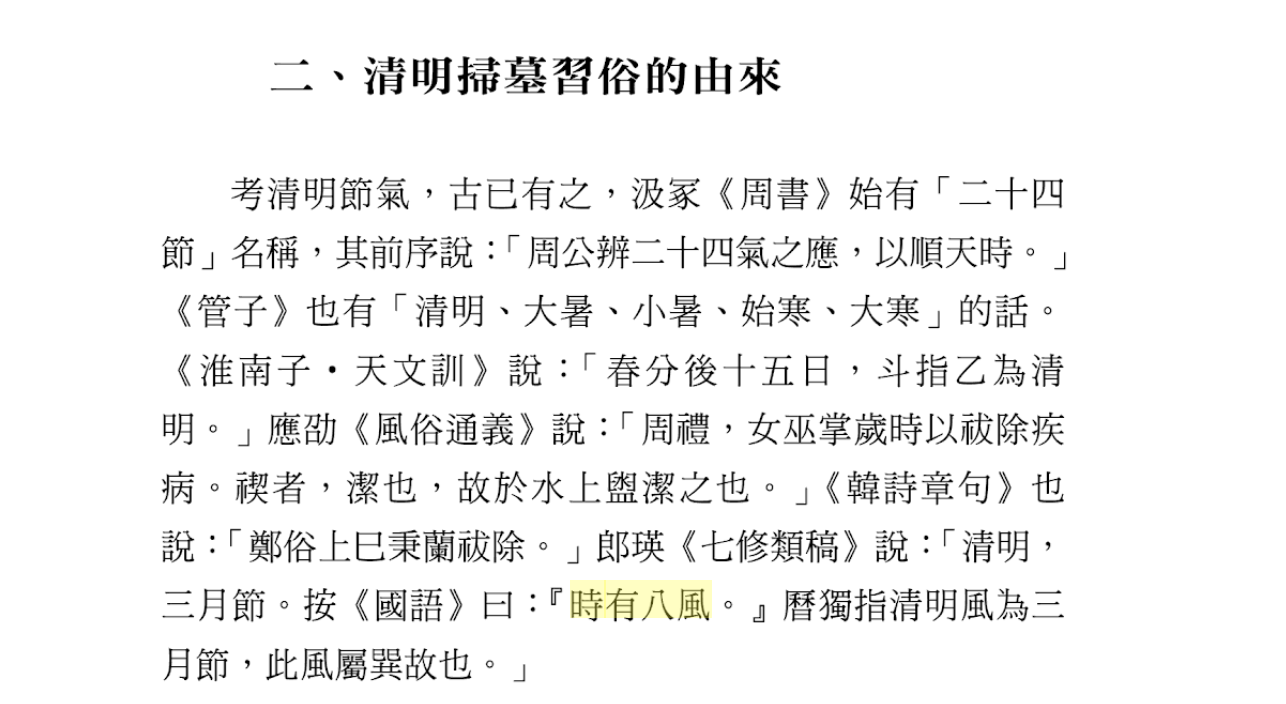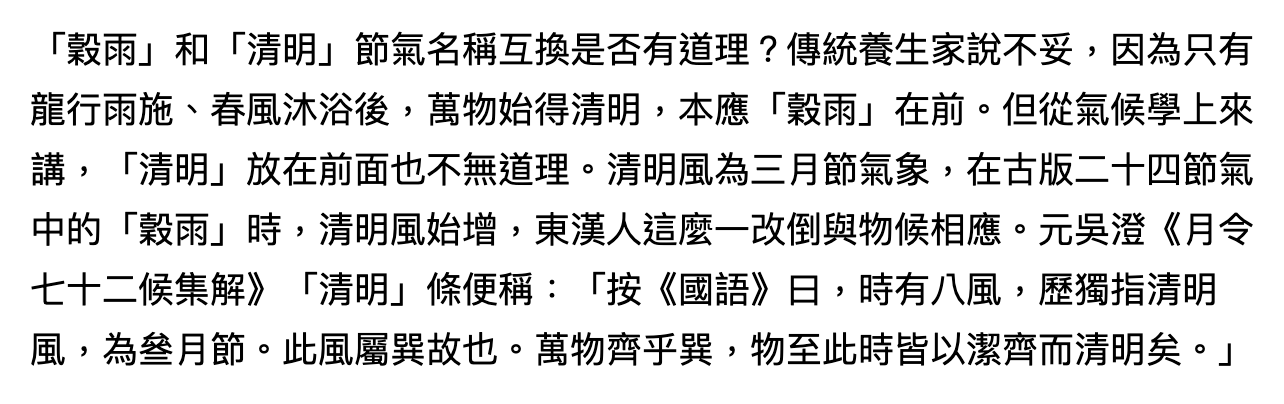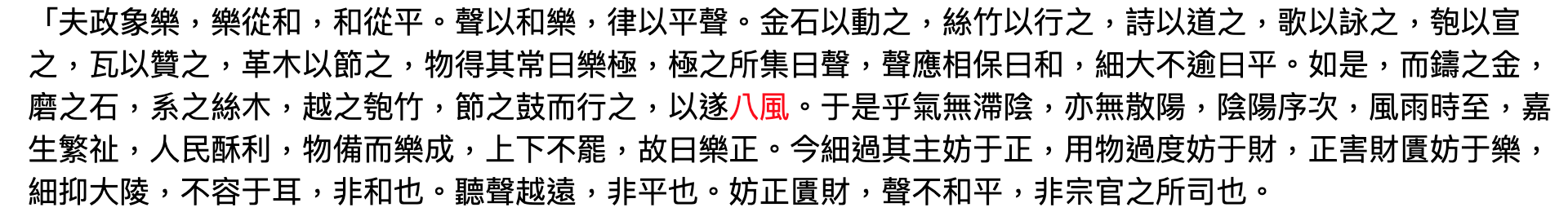如何判斷是不是真愛?很簡單啊,心跳有沒有加速?有沒有一天到晚就一直想著念著?發現自己又在想著念著的時候,會不會有一點臉紅心跳加速?
從這幾個跡象來判斷,這次應該是真愛了。
「我不認為有比希臘悲劇更悲慘的事了。」小時候讀的小說裡看過大概長這樣的字眼。沒什麼好爭辯的,年紀大了,即使自己最關心的事,在別人眼中看起來只是自己的肚臍眼也沒什麼關係。大概因為這樣,我愈來愈不喜歡一天到晚跟著網路上哪個新鮮的服務、應用跑來跑去,時間和力氣都花在新玩具的認識、調校上(哪來那麼多美國時間啊)。話雖如此,我還是會東瞄四瞄,以避免真的漏掉太寶貴的事物。
話雖如此(第二次了),我沒想到,這個老早就看到過的名字 WorkFlowy(從來不曾心動過啊),有一天,竟然會變成真愛。修成正果真的需要因緣具足。
有點不好意思承認,大概一個月以前,我才接觸到 notion,以為還蠻漂亮,蠻順手的。還貼了推廣的推文(順便賺點免費使用的空間),也真的玩了一陣子,的確是又好看、又方便。但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吧。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,大概一九九零年代吧,真的有了自己的筆記電腦,後來玩上 FreeBSD,在 terminal 的環境裡學習、遊戲、整理自己的想法、知識、念頭。(多次校調,經過數位政委唐鳳(那時候他的漢字名字和網路名字都和現在不一樣)加持過的 .vimrc 一直還待在我的 MacBook Pro 裡服役中。)
玩過架在自己電腦裡的 BBS、blosxom(真懷念的極簡風格 blog 系統),玩過賣掉之前的 tumblr 和一些有的沒的。自己的網站搬了幾次家,換了幾種系統、平台。到手持機器已經發展到強悍無比的現在,我真心喜愛的,還是架構和呈現方式都簡單一點的。
最好是簡單,但彈性又大。簡單,而又能強悍,得花點腦筋思考、布局、觀看、體驗、欣賞的強悍。
這次的 Seaside Rendezvous,碰上這已經有點歷史的 WorkFlowy(人家 2010 年就上線囉),心裡感嘆詞不停斷:天啊,差不多就是想像裡的樣貌嘛。(註記一下,這一次是因為看到淡水奶爸貼的介紹文,想說再多看一眼吧,看著看著,就「牢鼎」tiâu-tiáⁿ 了。)
前幾天在讀今敏的隨筆,《我的造夢之路》,講的是他的經典作品《千年女優》創造過程背後的故事,有一段話看得我非常激動:
小酒館裡的蠢話是百萬個夢,酒精是踢開緊閉的門扉的、無意識的寶貴一腳,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。前半句和後半句意義不明的話擺在一起,只不過是為喝多了找個理由。
我們的腦子就像是《千年女優》裡的老婦人,始終等待著什麼;但我們的腦子同時也是去採訪的社長、也是攝影師。真實和虛構交錯,光線和陰影互文。在 Workflowy 裡的各種層次、連結(超強的 tag 系統,就看你的想像力和規劃能力有多強)下,我從這個點挖下去,竟然從另一個地道爬了出來重見天日。挖自己的腦子真有趣。
好多年前,一位我本來想找來出本什麼書的潛在作者回我說,「可是我沒什麼話想和這個世界說耶」。當時的我,現在的我,都只能用力點頭稱是。其實我也是。但是我很願意和我的腦子裡的眾多小小人對話,讓他們說想說的話,聽他們說他們想說的話,有力氣的話,記錄一些下來,甚至回應能夠回應的。給自己看,給這些小小人看,給以後看。
對於出版,不論文本是什麼形式,載體是什麼形式,我以為當然必須要有很強烈的 agenda-setting 的意圖。用感動、觸動人心的方式、技巧,進而激發改變。改變讀者,改變世界,也回過頭來改變作者自己。讀者可以是外在的,也可以是內在的,腦子裡的眾多小人,committee 裡的眾多成員。沒有這點抱負其實也就不用玩出版,不論文本是什麼形式,載體是什麼形式。
Workflowy 的付費會員有自動備份的功能,但沒付費的人還是可以手動備份。我一開始手動備份成 .html 的格式下載,剛剛我又玩了一次,一隻 785KB 的 .html。我想像的畫面是這樣子的:花幾個月的時間,把手邊舊的、新的,有的沒的文字生產、筆記,全都整理到 WorkFlowy 上。最後整個人生、整顆腦子化為一件 html 檔,層次歷歷分明,有標題,有小註解,可查詢關鍵字。(看著立體感十足的全域查詢結果映入眼簾還真是奇哉妙哉,真是不亦樂乎。)
剛學瑜伽的時候超愛推銷,逢人就叫賣。現在懶了,自己練比較實在。如果你剛好也有興趣,很好,如果你剛好還沒興趣,那也很好。
如果你對世界上的知識、體系,對自己腦子裡複雜的資訊流有興趣,WorkFlowy 真的可以打造成超合身的強力工具(或者兵器)。當然啦,就像靜坐,表面上看起來,也就是這麼靜靜坐著,只有坐了「進去」的人可以感受到,那過程、體驗可以多麼趣味、複雜、而又迷人。WorkFlowy(或者其他任何你喜歡用的軟體、程式,或者空白的紙本筆記本也一樣),可以只是條列記下幾條備忘的瑣事,也可以搖身一變,成為探鑽腦子(又同時能夠紀錄下來)的瑞士刀。
我一直記得第一次清楚寫下 góa 正確標音的台文時的內心激動。那場景,大概就像是「上帝講:『著有光』,就有光。」有些時候,我記錄下一些似乎值得記的,有些時候,我回顧一些記錄,早已忘記事件的脈絡、細節,但一些味道、氣氛、光影,說不定還能在腦海裡勾勒出來。這幾個星期在 WorkFlowy 上玩耍時,我好多次感受到那勾勒的「過程」現形的快感。
對了,如果你也覺得有點心動,想試試看的話,可以按這個連結,你會因此一個月多個 250 則的用量。(嗯,我已經是付費會員,使用空間沒有限制囉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