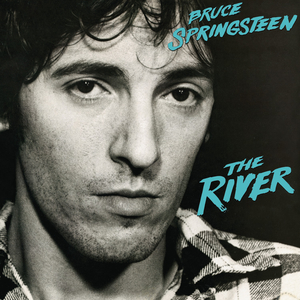Hiāⁿ-chháu kap phiò-pe̍h-chúi 艾草佮漂白水
Tâi-pak kin-nî khah chá kôaⁿ, tong-jiân sī bô lo̍h-seh, m̄-koh hō͘-sap-á it-ti̍t bô thêng. Kui-keng kàu-sek lāi-té sip-sip,ta̍k-hāng mi̍h-kiāⁿ kán-ná láng tài chi̍t-tiám-á chhàu-phú-bī, án-chóaⁿ tō bōe chheng-khì. Kui-khì iōng phiò-pe̍h-chúi kā chū-á chi̍t-tè-chi̍t-tè chhit, liáu-āu koh iōng hoe-chúi chhit tē-lī-kái. Sòa-lo̍h-lâi tiám hiāⁿ-chháu, chi̍t-sî eng-phōng-phōng, bē-su tī soaⁿ-nih tà-bông-bū kāng-khoán. Bô-gōa-kú, phiò-pe̍h-chúi ê bī oân-choân hō͘ hiāⁿ-chháu khàm kòe, m̄-koh chhàu-phú-bī iáu-sī chhin-chhiūⁿ soán-kí liáu-āu ak-chak ê sim-chêng, bô-khó-lêng lóng-chóng siau-sit–khì.
台北今年較早寒,當然是無落雪,毋過雨霎仔一直無停。規間教室內底溼溼,逐項物件敢若攏帶一點仔臭殕味,按怎都袂清氣。規氣用漂白水共苴仔一塊一塊拭,了後閣用花水拭第二改。煞落來點艾草,一時坱膨膨,袂輸佇山 nih 罩雺霧仝款。無偌久,漂白水的味完全予艾草 khàm 過,毋過臭殕味猶是親像選舉了後齷齪的心情,無可能攏總消失去。
Cháu-pio 走標
Chi̍t-khai-sí góa tio̍h-ài chi̍t-chhiú thê chhiú-ki-á, ná cháu ná thiaⁿ chhiú-ki-á pàng-chhut-lâi–ê liâu-phek-siaⁿ, kha-pō͘ chiah-bōe têng-tâⁿ khì. Tùi chi̍t-hun-cheng pah-peh-pō͘, liān kàu chi̍t-hun-cheng nn̄g-pah-pō͘. Chit-nn̄g-kò-goe̍h loái, khai-sí khah koàn-sì, mā khah ū chū-sìn, hō͘ chhiú-ki-á hioh-khùn, góa-ka-kī cháu, kán-ná mā ē-sái–tit. Lō͘-bóe to̍h lóng bián koh ke giâ-kê, siang-chhiú khang-khang cháu-pio pòaⁿ-tiám-cheng chi̍t-tiám-chèng mā bô-būn-tôe. Chêng-chi̍t-chām-á khai-sí ē-sái thiaⁿ im-ga̍k cháu, kéng chi̍t-kóa-á liâu-phek kap kha-pō͘ chha-put-to ê im-ga̍k, kéng kah siān–ah, to̍h hō͘ chhìn-chhài pàng, mā lóng bōe-khì éng-hióng–tio̍h. Put-jî-kò, chi̍t-ê-lâng tiām-tiām bô-siaⁿ-bô-soeh tī kàu-sek lāi-té cháu-pio, chi̍t-liàn kòe chi̍t-liàn, chi̍t-hun-cheng kòe chi̍t-hun-cheng, mā sǹg-sī chi̍t-khoán tín-tāng ê chē-siâm, hō͘ thâu-khak-lâi–ê khang-su-bāng-sióng tòe leh gô-lâi-gô-khì, ū-sî mā ē gô kah chiok tiām-chēng.
一開始我著愛一手提手機仔,那走那聽手機仔放出來的嘹拍聲,跤步才袂重耽去。對一分鐘百八步,練到一分鐘兩百步。一兩個月落來,開始較慣勢,嘛較有自信矣,予手機仔歇睏,我家己走,敢若嘛會使得。路尾就攏免閣加夯枷,雙手空空走標半點鐘一點鐘嘛無問題。前一站仔開始會使聽音樂走,揀一寡嘹拍佮跤步差不多的音樂,揀甲𤺪矣,就予凊彩放,嘛攏袂去影響著。不而過,一个人恬恬無聲無說佇教室內底走標,一輾過一輾,一分鐘過一分鐘,嘛算是一款振動的坐禪,予頭殼內的空思夢想綴咧遨來遨去,有時嘛會遨甲變足恬靜。
Ián-káng 演講
Āu-lé-pài koh beh khui-têng–ah, tē-jī-kái. Àm-sî lo̍h-chhia kiâⁿ tńg-khì chhù-nih ê pòaⁿ-lō͘, góa put-sî to̍h ka-kī leh liām, nā sió-ha̍k-seng beh-khì chham-ka ián-káng-pí-sài, chi̍t-kái-chi̍t-kái leh liān beh ián-káng ê kó. Ū chi̍t-kang ná kiâⁿ ná leh liān ê sî, chiah hoat-kak ka-kī liām–ê sī Tâi-gí, kóng-liáu koh chiâⁿ sūn, khì-sè cha̍p-chiok. Khó-sioh gún bú-á bô-hoat-tō͘ lâi thiaⁿ. Chăng-cho̍h-ji̍t-á thiaⁿ-kóng iū-koh tú tùi kip-chín sàng tńg-khì chhù-nih, pâi bô ūi thang tòa-īⁿ. Ba̍k-chiu-kim-kim lâng-siong-tiōng, gúnbú-á í-chêng tiāⁿ-tiāⁿ kóng chit-kù. Góa leh siūⁿ, chit-kái góa tī hoat-īⁿ ê ián-káng nā ū tio̍h-téng, hō͘ hoat-koaⁿ khah him-sióng leh, sī-m̄-sī tio̍h-ē-sái tńg-khì khòaⁿ gún bú-á, thàn iáu-ū sî-kan, thang tī i bīn-thâu-chêng kóng khah chē ōe hō͘ thiaⁿ.
後禮拜閣欲開庭矣,第二改。暗時落車行轉去厝nih的半路,我不時就家己咧唸,若小學生欲去參加演講比賽,一改一改咧練欲演講的稿。有一工那行咧那練的時,才發覺家己唸的是台語,講了閣誠順,氣勢十足。可惜阮母仔無法度來聽。昨昨日仔聽講又閣拄對急診送轉去厝nih,排無位通蹛院。目睭金金人傷重,阮母仔以前定定講這句。我咧想,這改我佇法院的演講那有著等,予法官較欣賞咧,是毋是著會使轉去看阮母仔,趁猶有時間,通佇伊面頭前講較濟話予聽。
Lí tang-sî beh-khì Ji̍t-pún chhit-thô? 你當時欲去日本𨑨迌?
Hit-kang iáu tī lí-siā lāi-té, pêng-iú hiông-hiông mn̄g chi̍t-kù, bô lí tang-sî beh-khì Ji̍t-pún chhit-thô. Góa soah bô-ōe thang ìn. Góa sim-koaⁿ lâi leh siūⁿ–ê, sī beh-khì Kî-lâi-soaⁿ, khì Pat-thong-koan, khì Tōa-bú-soaⁿ, khì chhiùⁿ Jī-chúi chit-khoán chhân-chng kiâⁿ-kiâⁿ-khòaⁿ-khòaⁿ ê lú-hêng, bô-siáⁿ-mih chhut-miâ–ê chhan-thiaⁿ. Kòe-tńg-kang chiah siūⁿ-tio̍h, bô-tek-khak môa-nî ē khì–o͘h, khì kiâⁿ きそじ, khòaⁿ きそがわ, kó͘-chá しなののくに, みののくに ê kū-chhù. Bián chia̍h siuⁿ-kùi–ê liāu-lí, bián tiám siūⁿ-kùi–ê chiú, mā bián-kóng siuⁿ-chē ōe. Ta̍k-kang tau̍h-tau̍h-á kiâⁿ kùi-tiām-chēng-kú ê lō͘, kàu lí-siā to̍h un-chôaⁿ phàu–loeh. Ē-sái mài ti̍t-ti̍t khai-káng to̍h-hó.
彼工猶佇旅社內底,朋友雄雄問一句,無你當時欲去日本𨑨迌。我煞無話通應。我心肝內咧想的,是欲去奇萊山、去八通關、去大武山,去像二水這款田莊行行看看的旅行,無啥物出名的餐廳。過轉工才想著,無的確明年會去喔,去行木曾路,看木曾川,古早時信濃國、美濃國的舊厝。免食傷貴的料理,免點傷貴的酒,嘛免講傷濟話。逐工沓沓仔行幾點鐘久的路,到旅社就溫泉泡–loeh。會使莫直直開講就好。